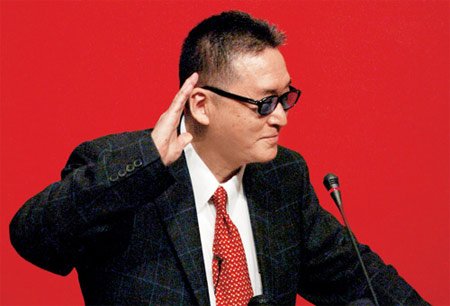
本文摘自《几度飘零》,古远清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李敖是海内外最受争议的人物。三十多年来,人们对他千夫所指,他对人们横眉冷对,唯独对胡适十分崇拜。上初中时,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《胡适文存》,读来如痴如醉,从此胡适成了他心中的偶像。1952年10月1日,十七岁的李敖在台中给胡适发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。1954年,还在上高中的李敖写了一篇论《胡适文存》的文章,迟至1957年3月1日才在《自由中国》刊出。从读到李敖在中学时写给他的信起,胡适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。这次读了李敖的评文,胡适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印象。发表此文的雷震还专门写信给胡适,要他特别注意李敖这位后起之秀。
1958年4月,从美国回来的胡适约李敖到钱思亮家,在谈话中胡适十分赞赏李敖治学的勤奋,称自己忘了的著作李敖居然能“找得到”,“你简直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”。除这次长谈外,胡适还在台大和“中央研究院”等处和李敖小谈过三次,并写过三封信给李敖。其中一封写于1961年10月7日,给“三条裤子都进了当铺”的李敖送上一千元支票。李敖收到后,深受感动。胡适原本是李敖父亲的老师,虽然李父当时不是拔尖人才,胡适已记不起他的模样。胡适对李敖的赏识,主要是看中李文不同凡响的才气,凭他的眼力就可知道李敖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台大学生。李敖选择在双十节那天给胡适回了一封长信,从自己的生平谈起,一直谈到自己在受胡适思想影响后,如何进入新的境界。
李、胡这时期打得火热,与胡适有意收其做弟子有关。1990年11月24日,李敖在《胡适与我·自序》中,引胡适给赵元任信中的话:“ 交友以自大其身,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 ,这是李恕谷的名言,我曾读了大感动。这是‘收徒弟’”的哲学!”接着又说:“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,意思是说,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;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。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,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。胡适名满天下,又喜欢交朋友,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,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,是虚荣的、虚幻的,聪明如他,不会不知道。所以他在热闹之余,未尝不存‘求士’之心。”这里讲的“士”,即徒弟。显然胡适求贤心切,十分看中李敖的才华。李敖也不辜负胡适的一片好意,花了许多精力和金钱去研究胡适。他当时发表的文章,清一色都是宣扬胡适。
李敖并非想高攀胡适,这纯粹是出自一位刚步入学界的青年对学术大师的尊敬和热爱。在胡适“保守的自由主义”影响下,李敖憎恨“暴力”和“以暴易暴”,主张“淑世的改良主义”和“和平而渐进的转移式改革”,并自称“不见谅于急进者的勇迈”。李敖在中西文化大论战中发表的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》,也在替胡适鸣不平,并对反胡言论一一加以批驳。这时期的李敖确像外界有人说的是“胡适迷”。李敖在给胡适的信中亦坦然承认,是胡适使他“在迷乱里,放弃了旧有的道路”,再加上李敖的西化论从思想内容到文字运用与胡适均有相似之处,因此在开始论战时便有人骂李敖在做“胡适的鹦鹉”,是专吃胡适饭的,只会写胡适的文章,拍他的马屁,另还有人认为李敖所发起的中西文化论战,其幕后策划者为胡适。
李敖虽然崇敬胡适,承继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,并给胡适的历史地位作过最充分和最崇高的评价,但李敖的远大目标是“要做一个伟大的人”,无论是傲骨狂思的性格还是对学术研究的态度,均与胡适有许多相异之处。如胡适生性温和,讲话婉转含蓄,而李敖追求的却是率真与痛快,只要是他认为错误的东西,均六亲不认加以激烈的抨击再抨击。胡适做学术研究与从政时不同,讲究“小心求证”,不喜欢把学术问题与政治扯在一起,而李敖研究学术的目的完全在于政治,为政治斗争服务。他最感兴趣的是现实政治问题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。基于这一点,他十分不满胡适“老是卖老货”,对胡适那种“好话说三遍”的态度愈来愈看不惯。
对胡适研究较透的人如徐高阮,早就指出李敖的西化论不是出自胡适,而是受“全盘否定主义者”陈序经的影响。尤其是李敖受国民党的封杀、压迫和蹲大牢后,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对蒋介石藕断丝连,对官方温情脉脉,而是和国民党水火不容,因而他后来不再相信“淑世的改良主义”可争取到自由民主,反过来认为国民党是一头“毫无诚意”的“老虎”,一头绝不能与之谋皮的“老虎”,只有实行“精英抗暴”和“甘地式抗暴”,才能争取到真正的自由民主。基于这点,李敖声明:“我的父亲是他(胡适)的学生,我并不是他的徒弟。”1960年1月12日,李敖在给启庆的信中表示了他“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”的情绪,评价胡适,“简直可说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!世上不该有像他这样不进步的思想家”。他开始后悔过去写的那些过分赞扬胡适的文章,厌恶别人再把他和胡适深深地扯在一起,以至一听人家说李敖是胡适的信徒,他就恼火。
李敖由过去对胡适的“捧”到后来对他强烈不满,都不是作假,而是出于心平气和的“静观”结果。李敖要做热情、叛逆、勇敢的“战士”,而不愿做胡适那种钻故纸堆,“整天所卖的竟是一些 饾饤琐碎 的旧货与霉货”的“院士”。“胡适之”的时代已经过去,当今是属于“李敖之”这种愤世嫉俗的“厌世家”的另一个时代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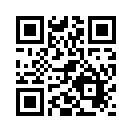 打开微信,点击底部“发现”,使用“扫一扫”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。
打开微信,点击底部“发现”,使用“扫一扫”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。